安史之乱爆发以后,首先是东京洛阳的达官贵人纷纷逃向荆襄一带,然后是唐明皇秘密逃往四川,接着西京长安官民逃往荆襄西蜀。所以荆襄一带居然一时出奇地繁华了起来。加之安史之乱持续了十年之久,洛阳两度失陷,对于避难于荆襄地区的中原富贵来说,可能也失去了回到繁华东京的信心。像李龟年这样的艺术家,当日在洛阳“大起第宅,儹移之制,逾于公侯”来看,安史之乱以前一直是过着超级富贵生活的。他虽避难荆襄,其生活应该还是富贵之风不坠的,而曹霸这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宫廷画师,只能以“屡貌寻常行路人”的避难生活度日。
二位艺术家的生活差异,或多或少反映出艺术命运的分配是很有差异的。

在唐代的艺术家中,我们所熟知富贵的艺术家,大概要数大书法家李邕最为著名了。据说他因拥有众多的墓志求书者,所以金帛至巨。《旧唐书》里说他因作碑颂“受纳馈遗,多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就是这样一位儒生眼中超级成功的文人,我看可能与李龟年的收入比起来应该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李邕生前可能想也不敢想“大起第宅”,更不必说“逾于公侯”了。李邕的钱,没有完全用来自己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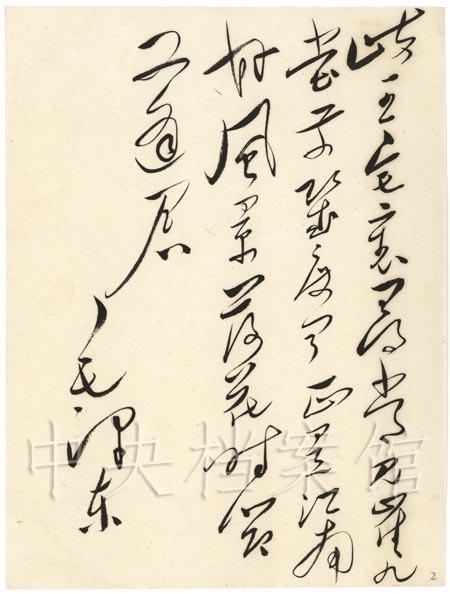
而曹霸更是不慕富贵,所以,一经安史之乱的浩劫,就迫于贫不能自给的困境了。难怪杜甫诗中说曹霸是“世上未有如公贫”的一位清门寒士了,看来这是非止一事的感慨系之。 同样的宫廷艺术家,同样的漂泊者,杜甫给予他们的同情也是同样真情同样惋惜的,这就是杜甫的情怀,这就是同样流离所失的杜甫,精神的浩气依然还是那么富足和充沛的诗人杜甫。
不过,杜甫究竟在何处与李龟年相逢?我们现在通行的说法是在长沙。好像唐代的一些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按李龟年的经济地位来看,立足长沙似不太可能。因为安史之乱以后,还没有逃到那样远的达官贵人。

杜甫在长沙时,并没有与高官作频繁交往,他怎么会在长沙见到高官的捧星李龟年呢?如果李龟年真的能与以舟为家的杜甫相见,那么李龟年的落魄则更不可想象,如果是这样,杜甫一定不会是以一首七绝句了事的,因为,那样的话,杜甫一定会从李龟年那里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而对于杜甫逢李龟年于何地,学者所引依据并不一致。见于长沙说者,以《楚辞》注“襄王迁屈原于江南”中的江南之地乃湘沅为依据,见于荆襄说者,以《史记·项羽本纪》中“徙义帝于江南”的江南荆襄之地为依据。二说看似都有道理,实际与分析杜甫的诗还是远了一些的。
从杜甫的诗而言,无论是江陵,还是长沙,都没有留下高欢筵集的诗。《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诗也写得很短,考察其写作地点的信息量非常有限。对于古人的考证我们就不多说了,这首诗写作地点的关键词是“落花”二字。

大致来说,落花季节就是暮春三四月之交。杜甫在长沙度过了两个“落花时节”的暮春。大历四年的落花时节,杜甫在长沙获韦之晋死。这一段时间里,杜甫极为困顿,整日以船为家,生活面比较窄,像李龟年这样富贵阶层圈里的人,在杜甫的环境中是很难遇到的。这一年的重阳节前夕,襄阳节度使判官刘十请他喝酒,杜甫虽然应邀到了酒店,但一向爱喝酒的杜甫,此时却好像一点兴趣也没有,就与刘十伤神而别。次年之春,杜甫依然在自己的小舟中度日,《燕子来舟中作》这首诗正是写于大历五年之春的作品。诗中写道:“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说明杜甫在长沙是渡过了两个春夏的。杜甫在长沙所居一直在舟中,而且自到长沙,好像连地方也没有挪动。大历五年四月十日以后,受长沙兵乱影响,杜甫起舟仓皇逃出长沙,不久去郴州不至,复自衡州北下潭州,是年死于去荆州的平江。
杜甫在长沙也接触过一些官员,但级别都比较低。杜甫因泊舟于码头,往往会有一些迎来送往,未能确信杜甫会在李龟年乘换车舟之时,睹其容而感慨赋诗,而且这首诗也不是赠李龟年之作。
《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诗,南宋之初的吴若本编于杜甫诗集之江陵时期。大历三年正月,杜甫自夔州之江陵。到达江陵已是暮春将至。但杜甫一到江陵,还是受到了江陵高官的邀请,成为座上一时宾。例如《玉腕骝》这首诗,就是对于荆南节度使卫伯玉宴请杜甫的记录。这里文人也较多。我的看法是李龟年应该在这一地区生活比较可信,江陵也是位于长江之南的。

江陵地区的行政长官卫伯玉,是一位生活豪侈的节度使。他广德元年镇江陵,那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完全结束,想必逃亡在荆襄地区的致仕富贵尚未尽归中原,像李龟年这样的鬐旧名人,更容易引起高官的重视,再说,他们也需要一些艺术生活的点缀,李龟年是会比较满意这种战乱中的逃亡生活的。
假如杜甫在这种背景下见到李龟年,其感慨叹息必然最深。因为,如此超级富贵的李龟年,好像已经消失多年,如何能在这样的地方一睹王府公卿座上的宠客呢?
对于诗中“寻常见”、“几度闻”最常见的解释是,杜甫少时洛阳的前辈引见他多次出入歧王宅和崔涤府(见社科院文研所1978版《唐诗选•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我以为这可能是误猜。李龟年是活到大历年以后了,可是歧王和崔涤开元十四年(726)已死。杜甫真能出入歧王宅崔涤府,成为寻常见几度闻李龟年的幸运少年之一,那么杜甫那样多的回忆诗文,为什么一次也没有提及这么值得难忘的事?而且杜甫向来是有这种美好感的癖好的。

譬如说,《壮游》一诗就写道“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可是此文之后,为什么没有“寻常见”“几度闻”李龟年的荣幸?要知道,歧王可是玄宗的长弟,歧王府更不是一般名流随意出入的场所。如果杜甫去过歧王宅,那杜甫一定会终身难忘的。其实,寻常见几度闻者,不是杜甫见闻于歧崔府第,而是杜甫在社会上早就多次耳闻李龟年出入歧崔之府的富贵宠遇如此罢了。

杜甫对于尽人皆知声名赫赫的李龟年,走红于公卿云集的洛阳朱门之间,略举一二例,以说明当日之显赫如此,此亦《丹青引》中写曹霸“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之手法。幸亏我们是知道杜甫开元之年没有进过皇宫,如果真进过皇宫,《丹青引》中的描写,一定会被我们认为是杜甫亲眼所见了。与曹霸承恩作画,非止南熏殿一处,李龟年寻常见歧崔王侯府邸必非仅此二家,都是一个道理,杜甫不过是用了艺术的手法转述了一些事实罢了。而“又逢君”一语,非复见于“江南”,乃昔日之耳闻竟成异时亲见于江南之谓耳。所以诗之标题对于李龟年之逢,“江南”这二字显得特别突出,那么诗中的“江南”,正是荆襄之地,盖诗人亦流落不定,感慨之深者在于此,顺便提一句,杜甫低江陵,也是他出峡而到江南之始。

实际上,把江南二字看做是长沙,好像也不太好解释。因为湘江北流长沙,陆地分为东西,并无南北之实可谓,说长沙是“江南”不是牵强了点儿吗?杜甫在长沙作诗,确是出现过“江南”一词。如《归雁二首》一诗就有“塞北春阴暮,江南日色曛”的说法,但那是出于对仗修辞之故,是广义地说长沙为江南,与《江南逢李龟年》中的特定江南是有区别的。如果一定认为杜甫是在湖南遇李龟年,那么衡阳正是在湘江之南的地方,杜甫大历四年春先长沙,后南下衡阳,长沙又是湖南的政治中心,湘江南来北去,说衡阳为“江南”是比较合理具体的。如杜甫在衡阳遇李龟年,从“落花时节”这个时间点和“江南”这个地理位置上来看,也许还有些意思。
不过,李龟年到底还是在荆襄一带比较合理。可以参照的,是杜甫著名的诗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据杜甫的诗序说,他五六岁时在故乡偃师,观看过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诗中又有玄宗开元年“先帝侍女八千人”之说,而安史之乱以后,已是“梨园弟子散如烟”的寂寥了。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一诗早于《江南逢李龟年》一两年,李龟年肯定也是玄宗“梨园弟子散如烟”中一员。

但李龟年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肯定比公孙大娘弟子的地位要高很多,公孙大娘弟子无奈只能在夔州这样的小地方演出维持生活,而李龟年是没有维持生活之虑的,所以,他应该在较为繁华的荆襄一带,仍旧与达官贵人为伍隐居。不过,杜甫所感慨者,乃是从一个富贵身上也能看到的安史之乱以后的社会大萧条是何等沉重。这种强烈的社会性的失落感,不论曹霸、李龟年还是公孙大娘弟子,都使得他非常敏感,何况杜甫赋《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一诗之后,到江陵却也是到了江南,所以杜甫在这个地方见到李龟年,那个落花时节的好风景,就显得尤其无可奈何的好了。